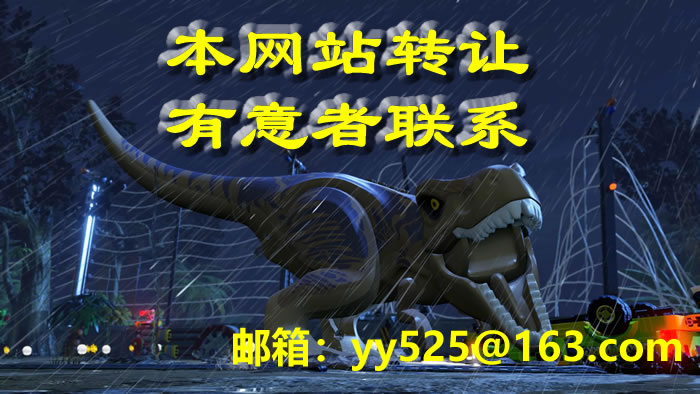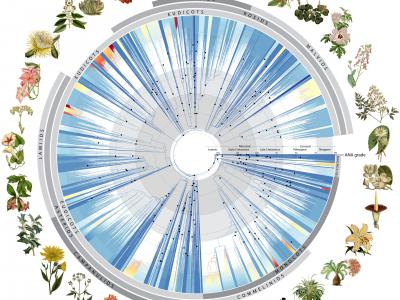卢梭晚年的植物学情怀
核心提示
卢梭声称,正是关于分类、排序和命名的知识,使“真正的植物学家区别于本草学家和分类学家”,字里行间隐约有以植物学家自居的意思。
对于卢梭是不是博物学家这一问题,他的自我评价与外界对他的评价并不一致。尽管在我们看来,如此热爱自然、天性浪漫又多愁善感的人,简直天生就具有一种博物学家的气质;更为重要的是,他的《植物学通信》曾引导很多人走上研究博物学的道路,甚至掀起一股以追逐博物学为乐的热潮,他在谈论植物问题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也曾启发歌德等人的灵感。但是,卢梭本人并不一定认同我们给他贴上的标签。
卢梭不认为自己是博物学家
从《植物学通信》的文本来看,卢梭仅有一处提到“博物学家”一词。相反,他一再强调自己是“植物学家”。他骄傲地声称,正是关于分类、排序和命名的知识,使“真正的植物学家区别于本草学家和分类学家”,字里行间隐约有以植物学家自居的意思。我们大胆地猜测其原因,可能有两点。首先,18世纪是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。百科全书派内部“数理科学骑士”与博物学家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,在当时学界看来,博物学多少带有几分民间科学的色彩(这种观念甚至直到今天仍然难以避免)。卢梭或许有意无意地同这一阵营拉开距离。其次,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,那就是卢梭只对植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与历史上著名的大博物学家,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、普林尼,以及近代早期的约翰·雷和林奈相比,卢梭显然缺乏对整个自然界的广泛兴趣。他将自然界中几个重要的领域排除出去,单单选中植物学来作为晚年孤寂生活的慰藉。对此,他本人的解释是“矿物界本身没什么让人愉悦的”,动物学研究则需要接触解剖室中那些“鲜血,恶心的肠子,可怖的骸骨,还有一股恶臭”。
深入分析卢梭的这种偏好,恐怕与18世纪的思想语境不无关系。在某种意义上,卢梭对植物学、动物学乃至矿物学的看法,首先是从当时理性主义的思想框架出发。以动物学为例,他首先想到的是“解剖室”、“鲜血”、“肠子”等。而在植物方面,他高度赞誉林奈的分类体系,并要求德莱塞尔夫人准备放大镜和解剖针,甚至声称这些仪器是“任何植物学家都不可缺少的”。
卢梭的植物学研究奉行情感主导进路
然而,卢梭本人在研究中并未奉行这种理性主义进路。虽然他极尽细致地论述了如何分解观察一朵花的各个部分,但是他更强调的是“从植物的位置上来观察它们”。他认为,标本只能“帮助我们回忆以前认识的植物”,却无法“帮助我们去学习未曾见过的植物”。因此,他一再要求德莱塞尔夫人亲自去观察植物生长的全过程,“如果你没有见过实物,我那些抽象的细节描述只会让你厌倦。要愉快而有用地学习大自然,你必须亲眼看到大自然的造物”。更多时候,他一时忘形,突然偏离植物教学的正题,开始严厉控诉人对植物的改造。他将人工培育的重瓣花斥为“畸形的怪物”,并告诫德莱塞尔夫人:要想欣赏“自然状态下”的果树,“千万不要去果园,而要到森林里去寻找”。在卢梭的植物学研究中,情感明显占据上风,理性只是他进行探索时的一种便利工具。在博物学研究的广阔范围中,卢梭唯独选中植物学,主要也是出于情感上的本能反应,而非一种理性抉择。正如他那种孩子气的表述中所说,他需要“明媚的花、碧绿的草地、凉爽的树荫,还有潺潺的小溪”来净化他那“被一切令人作呕的东西污染了的想象力”。在卢梭眼中,只有植物动人的色彩和形态,才能最直接、最充分地体现大自然纯粹的美。通过植物学研究,人们得以接触到自然界的奥秘,找到心灵的归宿。
历史上的博物学有很多种,既有理性主义主导的,也有浪漫情感主导的。卢梭无疑是后一种进路的开创者。在不同历史时期,博物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一样,有些是科学探索层面上的,有些是思想信仰层面的,还有一些则像卢梭这样,仅出于一种情感寄托或是博取外界认可的方式。
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往往不一定符合他实际的行为。卢梭曾自嘲他的“自相矛盾是众所周知的”。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矛盾色彩的人来说,这种不符合更加无足为怪。无论如何,卢梭充满情感与浪漫色彩的那种典型的“博物学式”植物研究,不仅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极大安慰,也给他的通信人,还有两百多年后读到这些通信的我们带来许多乐趣。更重要的是,他开创了一条情感主导的博物学进路。
中国社会科学报 熊姣(作者单位: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