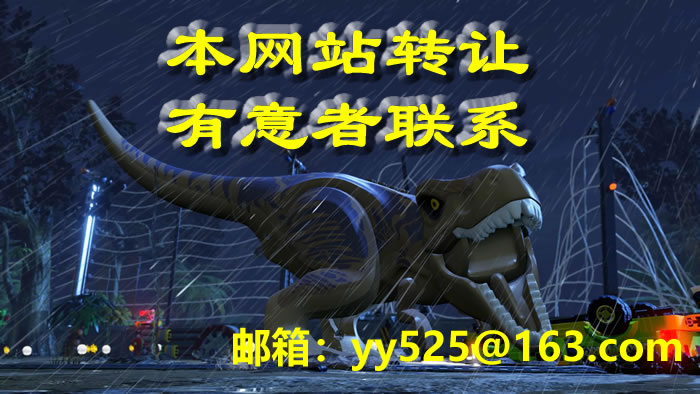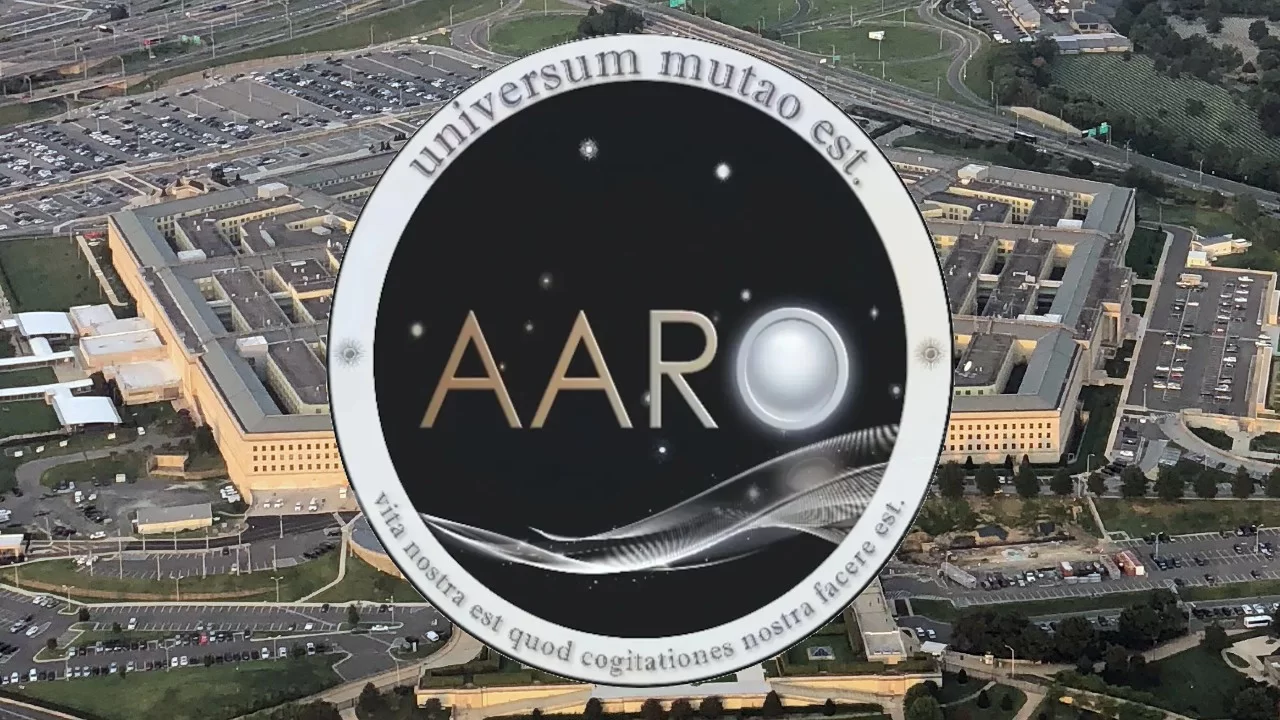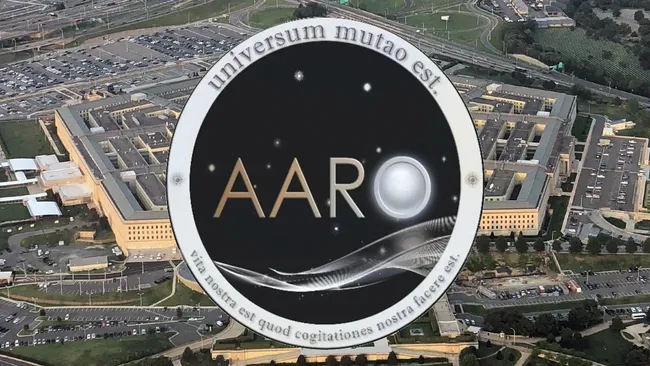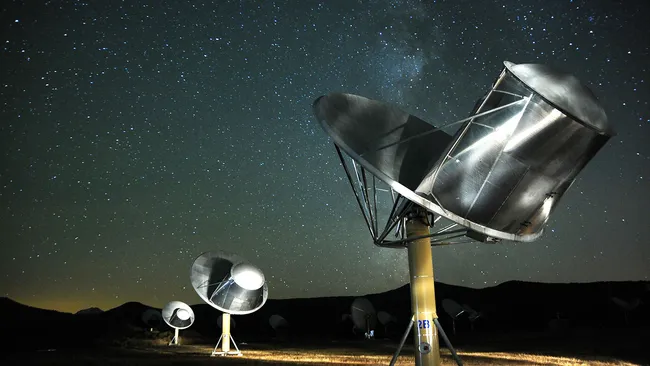英国解密UFO文件:冷战后目击UFO事件骤减
有一部分人操心就可以了
30年的时光,人们的视野在变化,人们接触资讯的渠道也在多元化,可以选择的兴趣点很多,科普杂志的市场越来越小众。
与此同时,原来的读者群也在流失。“我们在不断培养读者的同时,也是在失去他。从读者的角度说,这本杂志对他已经起到了一个启蒙、培养的作用。但当这本杂志让他了解了一些不明事物的事情以后,他可能就不看了,离开了。”何晓光已经感觉到了做科普杂志的痛苦。
“但是我们依然有职业自豪感。”读者的喜欢是编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《飞碟探索》的编辑们一起开玩笑说,十亿人民中要是有一亿人成天想外星人的事儿,这个国家肯定不正常,对于不明事物,有一部分人操心就可以了。他们觉得,太多人关心这些关于不明事物的事反而不好,“有一些人就说我整天想着这些事,都要有心理问题了。”
2010年何晓东去成都书市,一个40多岁的男人领着一个小孩,站在书摊前,男人一看杂志,“哦,飞碟啊”。何晓东心里明白,还是有很多人关注着《飞碟探索》,热爱对于不明事物的探索。杂志的编辑们也知道,很多人虽然没看过这本杂志,但是却知道它。更有一些人会很关心杂志的内容,关注杂志的发展。
有一个退休老汉,几乎每一期杂志出版后都会给杂志社写一些东西来探讨。从2009年开始,杂志推出找杂志中的错误的活动,每找出杂志中的一个错误,即得30元,有一些读者一直坚持下来。
还有读者曾经给杂志社写信,说自己的孩子天天想着2012世界末日,请杂志社的编辑们帮忙开导开导。杂志社的编辑就真的给孩子打去电话,交流了关于2012世界末日的话题。
何晓光说,有很多读者令他感动,也有一些人从一开始的读者变成了杂志的撰稿人。“原来我们杂志有个作者叫蒋明芳(音)是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生,给我们写稿子,后来出国了,突然有一次,他回国,就一起吃饭聊天。他说,他就是因为看了《飞碟探索》,才选择了现在的工作。”他现在在美国专门研究化石,解释历史和自然的秘密。
《飞碟探索》曾经做过读者分析,读者群基本是高中生以上年龄和学历的人,大学生比较多,也有40多岁的人。“可能就是有些人大学毕业以后坚持一段时间就不看了,但是到了40岁以后又开始找回《飞碟探索》,生活安顿下来了以后,又开始思考一些问题。”
人们对飞碟、不明事物的探索依然在继续,并且越来越渴望。“读者见面会的时候,他们来了就席地而坐,跟你讨论关于一个问题他是怎么想的。很多读者的专业性,研究的深度,确实也很让人佩服。他会给你找错误,他会跟你讲,如果是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。”
“这就是做这种杂志这种话题给你带来的乐趣。”社长何晓光说。
飞碟梦还能往哪走
何晓光在青岛上学时,已经是《飞碟探索》的铁杆读者,当时,他觉得这本杂志挺好看的,并没预料到学水文工程的自己之后会结缘《飞碟探索》。何晓光的儿子读初中,偶尔翻看一下父亲带回家里的杂志,也只是为了去同学那里吹吹牛,并不是真的喜欢看,他爱看的是日本漫画。
科普杂志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知识普及性,并不是每个人都爱看。而《飞碟探索》更是小众里面的小众。从过去一年发行30万册到现在每年只剩下4万多的销售量,看上去《飞碟探索》已经走进了瓶颈期。
很多老读者也给编辑部写信,担忧《飞碟探索》之后的发展道路。
杂志曾经的宣传语是“我们是国内唯一的UFO杂志,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UFO杂志”,但是现在已经无从标榜:面对网络媒体环境的冲击,人们接触关于UFO的资讯渠道更多也更丰富,平面杂志已经不具有唯一性,而在时效性上更是逊色一筹。如何留下老读者的关注又吸引年轻一代的目光,是《飞碟探索》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杂志曾经开辟了科幻小说的栏目,希望拓宽读者群,但是老读者们不太接受,最后还是取消了。
何晓光还想过给现在的杂志“建一个预备役”---创办《飞碟探索》的青少年版,用更新的形式和有趣的内容去吸引孩子,但是很多资源上很难实现。
对于之后的发展,何晓光说,产业化发展是必然的道路。“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俱乐部和协会”。
现在《飞碟探索》杂志已经推出了“不明现象之友”的俱乐部,有5000多会员。依托《飞碟探索》这个品牌,俱乐部的内容可以做关于飞碟探索的图书、天文观测仪器等等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借助俱乐部的形式探索未知事物和自然,可能更有利于做杂志。
何晓光对于未来仍有信心。“我们大家关注飞船、外星人毕竟是想知道人类将来的发展,往大处延伸,就必然要关注现在人类的周围环境,关注自身的周遭。”而从2004年开始,杂志的内容已经不再全部锁定UFO,而是渐渐地走向关注天文、宇航、考古、历史、地理⋯⋯
《望东方周刊》